假如你是一位作家,正在為中國的風險投資,編寫一部屬于從自我視角出發、定位自我軌跡的“行業史”,你會選擇一個什么樣的故事來切入人民幣基金的故事?選一位什么樣的人物來詮釋風險投資會在2005集體將目光看向中國市場?又會選擇一個什么樣的投資案例,來解釋風險投資的意義不僅僅在于赤裸的“盈利”?
這是投中網編輯團隊一年多以來反復思考的問題,而今年11月出版的新書《中國風險投資史》就是我們的答案。自立項到成書,用全書三十余萬字、共十四個章節,整理出風險投資如何在中國萌芽、起步、發展和蛻變的脈絡。
但正如投中信息CEO楊曉磊在編后記中說的那樣,由于篇幅以及其他客觀因素的限制,雖然這部《中國風險投資史》已經盡可能地做到了以“風險投資”為本,盡可能有臨場感的、帶有感性洞察地還原每個階段的橫截面,但終歸是有遺憾的。很多重要的命題并沒有積累足夠的一手素材,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我們也只能以一個更偏“旁觀者”的角度來論述,缺乏親歷者的洞察。
好在,這本書并不是我們記錄的終點。11月27日,在“第19屆中國投資年會·有限合伙人峰會”上,投中信息CEO楊曉磊、投中網總編輯董力瀚與書中的兩位主角——前海方舟董事長靳海濤、火山石投資管理合伙人章蘇陽,進行了一場以“我所經歷的《中國風險投資史》”的圓桌對談,一起聊了聊那些在書中沒來得及寫、沒來得及問的真心話。
以下為現場演講實錄,由投中網進行整理:
深創投和IDG,骨子里相同的內核?
董力瀚:各位好,吆喝了一年多,終于把書做了出來。今天借著這個由頭,把兩位老板請過來和各位一起聊一聊。
我先分享一個小事。前段時間我在整理IDG章節初稿的時候,有位朋友跑來找我喝咖啡,問了我一個問題:“IDG是中國最老、最頭部、最頂級的基金,為什么在投中網的報道里出現次數那么少?”——出現次數多的是誰,我們暫且不表。他的語氣更多是疑問,而非質問。
我當時回答他:“不敢。”
為什么不敢?我認為,從寫作者的角度出發,因為IDG歷史非常悠久,業務結構復雜,旗下基金數量多、團隊規模大,幣種也是兩種都有,導致我們不太敢輕易說自己真正理解它、能夠定義它,甚至去為外界解讀它。從選題難度來看,IDG確實是市場上最難寫的對象之一。
我隨后隨口反問了他一句:“你覺得這個市場上,有誰敢寫深創投嗎?”
而今天,當我坐在這里面對兩位老板時,我忽然意識到:盡管我從未將IDG與深創投這兩家機構放在一起比較過,它們從外表看差異極大,發展路徑也各不相同,但在我的潛意識中卻始終覺得它們之間存在著某種可比性,從時代背景、人的背景到思維方式,它們內里其實非常相似。
這個問題是我臨時想到的,之前并未與任何人溝通。我還是想現場請教三位對我這一“暴論”的看法。
靳海濤:IDG很早便進入開展風險投資,我認為它的貢獻非常大。深創投則是中國本土最早從事創業投資的機構之一——我始終持有一個觀點:本土創投的策源地在深圳。正是因為深創投的設立,帶動了一批各類資本進入這個行業。
IDG和深創投在風格上肯定存在差異,但所做的事情本質上是相近的。
深創投的風格是投資硬科技、投資制造業,這比較符合中國本土企業的實際需求。IDG也比較偏好偏早期的投資,相較于其他帶有美元基金背景的機構,在硬科技領域的投資比重要更重一些。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一批美元背景的機構主要遵循趨利原則,而這種趨利行為同樣推動了中國的發展和企業的成長。他們通常會參考在美國已成功的案例,然后在中國尋找相似的模式,去培育它,或者是發現它、推動它,最終幫助企業在海外上市,從中賺取差價。
我認為在互聯網時代,很多商業模式創新非常有特色。早期美元基金所投的項目,大多側重于與互聯網相關的商業模式創新,這些投資同樣具有重要價值。
IDG在兩方面都有所布局,但與等其他機構相比,它在制造業、科技類項目上的投資可能更具特色。
董力瀚:我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不斷思考人的行為方式、人在市場中的生存狀態,以及人對自我的認知是如何形成的。現在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時間點非常重要。比如2000年前后——IDG是九十年代開始做,深創投是2000年成立——那個年代進入行業的人,對自我的理解、對投資的認知,盡管使用的幣種不同,一方用美元,一方起初是國資背景,但他們在觀念底層上,可能與零幾年入行的人,或者像我們這樣四十多歲的人,對世界的看法不一樣。
靳海濤:其實一開始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前進,誰也沒有完全弄明白。我們做決策,往往受到過去所接受的思想和經驗的影響,會不自覺地沿著已有的經驗路徑去摸索。我理解,這可能是形成差異的一個關鍵。
從團隊構成上來看,本土創投早期的人員基本上都來自國內,有些可能出國學習過,但極少有在國外長期工作的經歷。而美元基金團隊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擁有海外工作背景,他們看到的、接觸到的以及積累的經驗有所不同,因此在選擇投資標的和做事方法上,也會形成一定的區別。
董力瀚:靳總剛才提到了“本土機構”這個概念,我想接著請教章總:為什么市場上會對IDG存在某種認識上的偏差?是否因為大家沒有把IDG看作一個狹義的美元基金?就像靳總所說,雖然團隊成員可能具備海外經歷,但在本質上并不算純粹的海外背景——我們的方法論是扎根于本土的,是中國人自己的方法、本土基金的路子。這個判斷放在IDG身上,是不是成立的?
章蘇陽:深創投在成立之初與深圳市國企有關,最早是由深圳市屬國企主導設立的創投機構。而IDG則是由熊曉鴿、周全等人從國外回來,逐步建立起國內的投資體系。
但有一點值得注意,IDG的合伙人團隊與15年以前已經嶄露頭角的許多知名投資機構相比,有一個顯著的不同:IDG的核心合伙人絕大多數原來都具有體制內工作經驗。
例如,有四機部出來的、中科院著名大所出來的、國務院發展中心出來的、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有國內重點企業出來的等等。這些人在體制內時大多已達到處級干部。
我認為這一點在IDG在內部管理和對外宣傳等方面的基本風格是有影響的。
舉個例子,當年我們組織團建外出旅游時,如果有員工不慎跌倒,周全肯定是第一個上前把人背下山——這種作風就帶有很深的體制內早期干部的風格,很多行為準則都是以互相負責和看重他人貢獻為重的。再分享一個細節,已經過去這么多年,不妨稍微揭秘一下:IDG高級合伙人內部曾有一項約束規定,兩人以上不能去商K,因為三人為“眾”。
董力瀚:請客戶也不行?
章蘇陽:基本上沒有例外。此外,IDG當年入局很早,從投資邏輯上看,它本質上是在投趨勢——當然,現在的趨勢和當年已不太一樣。當年的互聯網興起,是一個巨大的時代趨勢,而且互聯網的發展與人口密切相關。IDG事實上抓住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風口,再到后來的移動互聯網,它也基本都踩準了節奏。
而現在的風口周期短了很多,一個趨勢往往兩三年就過去了,而當年的趨勢相對更長期、更穩定。因此,當前投資面臨的困難肯定比當年更多。
這背后還是與合伙人的基因有關。但是IDG從一開始就是美元基金,內部并沒有太多條條框框的約束,形成了一種比較特殊的文化。它和那些完全由純海歸背景或外籍團隊建立的純美元基金有所不同——盡管投資方向可能與后來的美元基金相近,但從內部文化來看,確實存在一些差異。
這批合伙人絕大多數都是從體制內出來的,而且大多在體制內承擔過一定職責,屬于骨干力量;同時,他們也在國外接受教育和企業的體系訓練,所以,IDG的文化其實更傾向于是一種混合的產物。
董力瀚:那么曉磊,你作為一個觀察了這個行業十幾年的旁觀者,對這個觀點怎么看?
楊曉磊:兩位老板其實已經把IDG與深創投的異同講得挺清楚了。我分享一點個人感受吧,畢竟觀察這個行業也二十年了。有一次我去看話劇,看到藝術家在臺上表演,當時有一個特別明確的感受,還發了一條朋友圈。我說,那些真正優秀的人,不管在什么行業,都是“閃著光”的。我接觸過很多投資人、企業家、藝術家,他們身上那種總體的感染力其實非常相似。
回到IDG和深創投,包括兩位前輩也一樣,只要是在這個行業里最終走向頂尖的人與機構,在外人看來,也許具體操作、風格、路徑略有差異,但結果是相同的——他們都帶著一種“閃著光”的氣質,擁有非常顯化、外放的情緒。這真是我的真實感受。
董力瀚:但是呢?
楊曉磊:沒有“但是”。他們給人的直觀感受就是如此。
至于形成這種氣質背后的原因,剛才章總已經對IDG的人員構成進行了解讀,那可能是塑造過程的一部分。但從結果來看,頂尖機構和人物給人的確定性是相似的。從外部看去,它們或許像一座座“深宅大院”,但在與行業互動時,都展現出那種光芒感,傳遞出強烈的確定性。
人民幣基金和美元基金,適用同一套“評價體系”嗎?
董力瀚:接下來我想問一個略帶矛盾感的問題。章總,上回楊曉磊和您做訪談時,你們聊了三四個小時,我仔細看了聊天記錄,印象最深的是你們談到一個觀念問題——無論是二十年前還是十幾年前,大家對人民幣基金、對國資背景的機構,無論是說帶有歧視、偏見還是評判標準上的差異,這其實是有問題的。這次寫書時我認真思考了這個問題,我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
比如剛才靳總的話里話外,我的理解是,IDG某種程度上是“抄過作業”的,而深創投則“無作業可抄”。當然,您在那個時候投出攜程、土豆非常了不起,但這些投資背后有跡可循,有海外已驗證的知識可供借鑒。當你研究、學習并嘗試線上商業模式的可能性時,就有可能捕捉到那些機會。
但對當時的人民幣基金市場來說,這仿佛是另外一個“工種”。盡管表面上都用錢做投資,但實際上市場環境不同、觀念不同,甚至完全沒有任何現成的路徑可以參考。
靳總,希望您能就這個問題在現場再回溯一下——您認為當時大家沒有真正理清的核心是什么?比如當時深圳有很多人民幣基金,普遍會說“我們要學習美元基金”,要學它們的勇敢、押注和承擔風險,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夠賺錢。如今回過頭看,這種認知是否本身是一種誤解?人民幣基金的發展路徑本就不是那樣的,本質上可能已經不是同一個“職業”了。
靳海濤:這其實與團隊人員的構成相關。就像剛才蘇陽提到的,IDG的團隊雖然有體制內的背景,但他們畢竟在國外待過一段時間,甚至較長時期。而人民幣基金團隊的成員,大部分成長和發展都在本土,他們所觀察到的、所接觸到的東西,與美元基金團隊是不一樣的。因此,對于新的商業模式,在理解程度和認知層面上自然會產生差異。
董力瀚:您認為有差距。
靳海濤:這主要源于投資團隊的視野與專業特長不同。像深創投這類人民幣基金,團隊成員背景往往更擅長科技與制造業領域,自然也就選擇了這個方向。
而很多美元機構更傾向于關注商業模式的創新,尤其是圍繞互聯網等大賽道進行布局——這類投資往往更具“震撼性”,潛在收益空間也看似更大。
但回過頭來看,收益并不絕對。投資科技類、制造類項目同樣可能獲得極高回報倍數。只是在那個特定階段,科技與制造看起來“不夠性感”,而互聯網則顯得“足夠性感”。在行業評價體系中,“性感”的項目往往更容易獲得更高關注。
董力瀚:那“性感”又是誰來定義的?這種觀念由誰塑造?到底什么算性感?
靳海濤:“性感”通常指向那些具有創新性、顛覆性,或代表未來趨勢的領域。比如現在大家認為人工智能、半導體很性感,而不再像過去那樣追捧互聯網。每個階段都有更細分的“性感”賽道。一旦被貼上“性感”標簽,資本市場往往會給予更高估值,財務指標的重要性則相應被淡化——在過去的互聯網行業也是有這個特色。
相比之下,傳統行業的市盈率、市銷率通常難以達到互聯網行業的高度。
當然,如果企業本身做得足夠出色,逐漸獲得市場認可,財務表現也十分亮眼,其估值也能水漲船高,為投資者創造可觀回報。事實上,即使在過去條件不如現在完善的情況下,投資制造與科技領域獲得五六十倍、甚至百八十倍回報的案例也屢見不鮮。但輿論往往忽略了這一點,習慣于用是否“性感”來評價一家投資機構的實力——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董力瀚:所以您認為,回過頭看,我們觀念中需要“去魅”的,正是“性感”這類抽象且不夠明確的標準?
靳海濤:過去國內往往直接沿用國際的評價體系來評判本土創投機構,這可能并不完全公平。有些機構投出了非常扎實的財務回報,數據很好,但卻被忽略了。當時的評價邏輯是:如果你投出了一個知名度很高的明星項目,哪怕只有一個,行業評價就會很高;而另一家機構即使投出了十個都成功上市、表現穩健的企業,但如果這十個項目都不夠“性感”,反而可能不如那一個明星項目受關注。這種“十個成功不如一個性感”的現象,在過去確實存在。
董力瀚:章總,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章蘇陽:其實這兩類機構與投資風格,現在已經越來越接近了。當年之所以形成差異,是因為所投企業帶來的商業價值與社會影響不同,進而導致輿論和宣傳層面的分化。從90年代到2015年前后,隨著互聯網普及,輿論場逐漸由30歲以下的年輕群體主導,他們所關注和表達的,往往更偏向于“性感”的內容。社會主流輿論在那個階段并不總是反映真實價值,但它確實形成了強大的聲量,也讓更多人接受了這種認知。
目前這種投資的相對同質性狀況大約在2016年代之后逐漸發生變化,到今天,評價標準已經趨于一致。
董力瀚:我還是想回溯一下:比如在2000年或零幾年的時候,如果說和當時的美元基金,相比起人民幣基金“有更多的作業可抄”,因此沾了光,您能接受這種說法嗎?
章蘇陽:可以這樣理解。當時國內真正屬于自主原創的模式只有兩個。一個是馬云的阿里巴巴——在它之前國外并沒有完全相同的模式,后來的淘寶是學eBay的模式。另一個是2003年江南春的分眾傳媒,在電梯里做的廣告業務,國外當時也沒有同類形態。除此之外,其他項目大多能在國外找到對應的早期產品或模式原型。
董力瀚:那您在當時有“抄作業”的覺悟嗎?比如在看攜程、土豆這類項目時?
章蘇陽:當時投資互聯網的邏輯,和現在看實業項目是相似的,就是看國外是不是已經跑出了成功的大公司。在攜程之前,美國已經有Expedia,Expedia現在也是比較大的。我們當時就想,中國未來旅游市場空間廣闊,難道不會出現自己的“Expedia”嗎?這個邏輯非常樸素。不要以為只有他發現這一點,都是差不多的,其實沒有那么“偉大”的東西。
董力瀚:章總太坦誠了,真的特別好。
章蘇陽:很多故事都是后來被神話的,這也跟互聯網本身容易放大噪聲有關。
董力瀚:接下來我問個更“刺激”點的:大家都說市場對人民幣基金存在偏見,兩位老板也承認確實存在,那曉磊有沒有這種偏見?而且你是做榜單評價的,某種程度上,行業的評判標準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你們手里。你來談談自己的想法。
楊曉磊:今天情況不同了,但往前推十年、十五年,整個行業的輿論語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某種外部體系主導和滲透的,在當時很多語境中,美國價值觀的傳遞是非常強勢的。舉個例子,如今中國有這么多主題樂園,但你很難想象在美國能建一個由中國人控股的主流主題樂園——對方的滲透力和話語傳播能力非常強。在2000到2015年左右的那段時期,我們這個行業的語境基本是以美國的話語體系為主的。
我們公司2005年創業,等于是進入這個行業“學習大人講話”。我們就像小孩學說話一樣,都是這么成長起來的。在那個階段,我們學習的就是當時的語境,向海外學習,向我們心目中“經典的美元VC”及其評價體系學習。
所以結論是——我承認。
董力瀚:這鍋你背了。
楊曉磊:記得在2016年左右,當時有一家機構發布了全球性榜單。我當時就提出,這類全球榜單的評價體系對中國投資人其實并不友好。因為在當時的語境下,中國市場本身就是一個不太被重視的市場,中國投資人也很難獲得那個體系真正的關注。
就像剛才靳總提到的,哪怕一家機構一年內投出十個IPO項目,在當時的全球評價視野中依然可能默默無名——這正是受制于傳統經典的評價邏輯。在美國主導的VC敘事中,投資機構的職責被定義為找到早期項目,注入資金,并為其構建一個宏大的成長故事。
但從2015年至今的這十年間,隨著整體格局與外部環境的變化,出資人的偏好也在轉變,大家對流動性的要求越來越高。這時候,什么才是“正確”的投資策略?是堅守一個可能需15、16年才能退出的巨型項目,還是選擇能夠更快為出資人實現流動性、并帶來超越市場平均回報的路徑?
因此,從那時起,我們開始有意識地調整自身的評價標準和規范。直到今天,我承認原有體系的慣性依然存在,那種經典邏輯能夠長期延續,自有其合理之處。我們不可能全盤否定,也不能簡單地“從左倒向右”——非此即彼的“二極管”思維并不可取。
我們正在做的,是漸進式地優化評價體系,這個市場最終應該對誰負責?對LP負責。
董力瀚:我希望你能講得更具體一些。我大致理解你剛才的意思,你認為投中榜單比某些國際榜單更適合中國市場,或者說你們的見識比他們更懂中國。但我更想知道的是,假設在2014、2015年你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在那個時候你能做什么?
楊曉磊:我們當時主要把關注點轉向了"流動性"。過去我們更多是看誰投了什么明星項目,但后來發現很多投資長期無法實現退出,這對出資人來說是個很大的困擾。
董力瀚:你的意思是,從那時起你們開始更注重考察它與LP之間的實際交付?
楊曉磊:對。過去我們更關注投資了哪些明星項目,特別是在移動互聯網線上線下融合的時期,很多企業快速崛起又迅速衰落。在那個階段,由于更側重投資端的表現,所以在評價權重和視角上也會相應傾斜。
但從那個時間節點開始,我們更加重視機構能否真正為出資人、為LP帶來流動性和回報,在退出端、流動性這些維度上投入了更多的關注權重。
在風險投資行業里,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友情”?
董力瀚:想現場問三位一個關于“人”的問題。作為一個步入中年、也有不少困惑的人,我很需要聽聽像您這樣比我年長、閱歷更深的老板們,對于人生和人際的感受。
前幾天我看到馬斯克在一次直播中感謝了一位叫巴倫(Baron)的投資人。那是一位華爾街的老頭,早年投資特斯拉賺了幾百億美金,兩個人處得不錯,是大家兄弟一塊賺過錢的交情。后來在馬斯克張牙舞爪收購推特、備受外界質疑甚至攻擊的時候——當時推特作價最高四五百億美金,當然后來降價了,大家覺得你是“神經病”嗎?誰會給你出錢讓你去買推特?——那位老先生卻主動找到他,拿出一億美金說“你先用著,我看看能不能再幫你找些人”。
馬斯克在直播里跟老頭聊天就哭了。他說他從沒主動開口向對方要錢,也沒想把他當作單純的“金主”,他們之間是朋友。老先生在那時候的舉動,讓他覺得自己在這行能交到朋友,有他這樣的朋友自己還挺感動的。
我就在想:在我們這一行,真的能交到朋友嗎?在中國做投資,能交到那種可以“過錢”的朋友嗎?我們常說朋友之間盡量別談錢,別借錢,否則容易傷感情,甚至有錢就沒朋友。而兩位在過去二三十年里,一直在金錢的博弈中打滾,又取得如此成就——你們覺得,這行里有沒有真正的朋友?
靳海濤:國外基金確實有這樣的傳統,他們通常不傾向于做平行式基金,而是按順序設立一期、二期、三期這樣推進,背后的LP重復度往往很高。如果你做得好,雙方的合作關系就會持續下去;即便某一期基金表現稍弱,但只要彼此關系融洽、LP也理解,就很可能繼續支持你——這是國外常見的模式。
而中國的資本構成不太一樣。國內并非沒有長期資本,比如家族財富本可以扮演這一角色,但由于國內誠信環境仍在發展中,很多人對他人信任度有限,再加上對風險投資這類資產類別的理解還不夠深入,要讓一個家族財富持續投資于同一家GP管理的多期基金,難度比較大。
另一方面,國內資本的管理方本身也在不斷變化。例如國資體系的領導會調動,地方政府的官員也會更替,在這樣的背景下,要讓資本方持續青睞某家GP,其實并不容易。當然,我們過去管理的基金中也有持續獲得支持的案例,存在認可我們的LP,但這類穩定合作的比例,比起國外基金要低很多。
董力瀚:您可以不具體點名,隨意舉個例子——比如至今仍與您保持著朋友關系,并且彼此有過合作的伙伴?
靳海濤:其實大家都是朋友,但人與人的關系會發生變化。有些投資人認可你,也未必會持續投資你的每一期基金——這背后原因很多,可能他資金狀況有變化,也可能他覺得其他方向更有吸引力。但這并不影響彼此繼續做朋友,大家依然可以交流意見、保持聯系。
但機構層面就比較難了。機構人員變動頻繁,所謂“機構持續喜歡你”往往與具體的人有關。即便你為它創造了很好的回報,換了領導后,對方未必繼續認可你。當然也有認可的,但概率上不穩定。若要說在困難時刻、風險很高的時候,還能有“哥們”毫不猶豫地站出來支持你——這種情況確實相對少見。
馬斯克是一個特例,他本身就和別人不一樣,他的朋友也與眾不同。這不具備普遍代表性。
董力瀚:我一直覺得靳總是個很有江湖智慧的人。
靳海濤:為什么不常做平行式基金?主要是擔心利益沖突——你讓誰啃骨頭、誰吃肉?但在中國,募資環境并不寬松,很難單期募到很大規模,所以往往需要通過平行式基金來達到一定管理規模。
不過,中國人在處理平行式基金時,會通過讓每個基金特點不一樣來規避利益沖突。有意思的是,中國投資人似乎對利益沖突問題不太在意,很少因此較真;而國外則非常重視這一點。
董力瀚:聽下來,靳總覺得我們其實處在更復雜的環境里,無論是工具還是職業屬性。我個人也有類似的感受,總覺得人與人之間似乎最后非得鬧掰才行,只是時間問題——沒錢掙了大家自然會鬧掰,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我感受上是非常不好的。
章總,您也談談您的看法。
章蘇陽:美元基金的運作邏輯相對單純。如果你的基金持續發展且業績良好,與他們的合作關系往往具有較強確定性——尤其是國外的母基金,只要你保持前進勢頭、表現穩健,他們基本上每期基金都會跟進。
而國內的情況則不同,正如剛才靳總所說,他在這方面了解得比我深入得多,國內并不完全遵循這種模式。當然,若論個人情感聯結,我認為馬斯克之所以感動落淚,是因為在美國的文化中,“你的事是你的事,我的事是我的事”是普遍共識,而當有人突然將“你的事”視為“我們的事”,這種跨越界限的支持就顯得尤為珍貴。他們的人際關系相對簡單清晰,彼此界限分明,最多也就是一起到酒吧小酌一杯。不像在中國,往往需要經過更深入的交往才可能建立這樣的信任。
國內的環境確實更復雜,靳總已經分析得很透徹。但從個人層面看,國內也有不少案例——有人每一期都投資你的基金,堅定支持你、認可你這個人,無論你做什么他都愿意跟投。不過這種關系更多是建立在私人對私人的基礎上。
董力瀚:那么當金錢因素加入后,這種關系還能保持嗎?
章蘇陽:我說的這些都已經包含了資金維度。再好的關系,若不涉及資金往來或許輕松自在,加了錢以后關系就會變得沉重。即使沒有資金往來,朋友可以陪你玩到凌晨,但一旦成為投資人,關系性質就變了。
不過即便如此,在國內的個人投資者之間,至今仍存在這樣的情誼——我就是認可這個人,就是看好他,當然他本身也做得不錯,各方面都值得信賴。國內環境中最怕的就是不靠譜,而不靠譜的情況確實不少。當你在社會上歷練十五年以上,自然就能分辨哪些是真正可靠的關系。
所以,真情依然存在。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若有人愿以真情相待,這份情誼就值得尊重和珍惜。因為不管國內和國外,現在真情這個東西還是挺寶貴的。
董力瀚:曉磊,你聊聊,像我們這樣的80后,面對GP時對方都是行業大佬,輩分上有差距,要真正交朋友其實并不容易。你在這行有沒有交到過朋友?如果交到的話,是什么契機?你又如何看待這種關系?
楊曉磊:作為第三方機構,我們的立場決定了原則上不應與行業伙伴建立過于密切的私人關系。如果要用尺度來衡量:一分是仇人,九分是血脈相連的好兄弟,五分是正常的商業往來——我對自己的要求是永遠不要超過七分。因為作為第三方機構,超過七分的關系其實很危險,我個人認為這存在很大風險。
此外,第三方機構與行業的互動本質是B2B的。我始終要求自己:不要把個人身份凌駕于機構身份之上,永遠是“投中信息”這個平臺在服務行業、服務大家,而不是我個人。
于理,就是這么一個理;于情管好自己就行了。至少過去這十幾、二十年,我都是按照這種方法來要求自己的。
從結果來看,是否與這些前輩建立了深厚的朋友關系?我認為很難。首先是剛才提到的職業要求限制,其次確實是因為人生觀與世界觀的差異。不同時代背景塑造了不同的世界觀,我們這代人的認知方向與他們那代人確實不同。包括去年與一些90后投資人交流時,我也感受到類似的隔閡——這種代際差異確實客觀存在。
董力瀚:人家拿你當老登。
楊曉磊:這個問題始終存在,客觀上也源于世界觀的顯著差異,這兩者交織在一起,共同塑造了現在的局面。
在具體方式上,我的做法很簡單:比如我個人從不主動組織大型飯局,也很少參與這類場合。置身其中總會讓我感到難以自處,角色定位也會顯得尷尬——這也是大家很少在飯局上見到我的主要原因。
你會如何想象十年后的自己?
董力瀚:如果要對10年后的自己提問,假設那時還有這樣的主題、這樣的書籍、這樣的對話機會,而且兩位對人生的認知可能又有了新的變化——如果十年后我們四人還能重聚在這里,你會留下一句什么樣的話。或者,你想問十年后的自己一個什么問題?
靳海濤:十年后肯定會比現在更好。
董力瀚:這個回答太實在了,正是值得十年后兌現的一句話。
章蘇陽:我記得小時候語文課本里有這么一句話:"是咱們這輩子沒福氣,讓兒孫們見到了社會主義。"我和靳總的看法差不多,十年后一定會更好——這讓我立刻想起了小學課本里的那句話。
董力瀚:希望到那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能更加緊密。
章蘇陽:從國家整體層面來看,人與人的關系我相信會越來越好。但具體到個體之間,說實話,我真不知道,既不確定自己,也不確定他人。但這并不妨礙我形成一個基本判斷:會越來越好。
靳海濤:觀察人類歷史,我認為人的本性中存有“惡”的一面。“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我更傾向于后者。若非如此,從非洲走出的猿人不可能演化至今——激烈的生存競爭需要這種“惡”。但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惡”的激烈程度在降低,其表現形式也趨于緩和。從這個角度看,人與人的關系確實可能比過去更進步,即便仍有沖突,表現形式也會溫和許多,對人的沖擊也相應減小。當然,人性中的“惡”難以根除,或許再過多少代仍會存在,但我認為會持續緩和。在某些環境寬松的階段,人性中“惡”的表現甚至會非常微弱。
董力瀚:因為那時不需要展現“惡”。
靳海濤:對,競爭激烈了,就會變成這樣。
章蘇陽:我再補充一點:十年后,肉身與肉身之間的直接接觸會越來越少,就像現在這樣,很多真實的感受可能無法直接傳遞。許多互動將通過更標準、自動、甚至AI化的方式進行。那時,人們可能會將很多情感因素從個人決策中剝離。肉身之間的成見有可能因此減少,但矛盾也可能轉移到那些已脫離肉身載體的意識層面——那些沖突或許會更為激烈。不過我感覺,肉身之間的直接矛盾確實有可能降低。
董力瀚:您的意思是,科技會往前走,文明會不會、人和人會不會,不好說。
楊曉磊:我相信未來世界會更好。如果十年后回看今天,我希望那時所處的行業、社會與世界都已變得更好,并且這其中,能有我一點點微小的貢獻。
董力瀚:你現在已經有貢獻了,謝謝三位,希望有機會十年后再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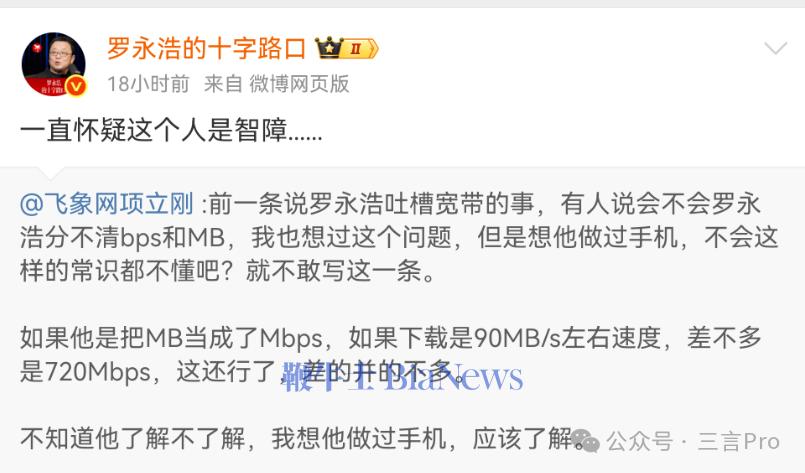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140201353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140201353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