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底工信部印發《人形機器人創新意見》,2024年被稱為“人形機器人元年”,2025年“兩會”熱議融合大模型與機器人的具身智能。種種跡象表明,機器人將不再被局限于工廠的勞動場所中,很快將大規模出現于日常的家居環境中,人機情感互動將成為未來智能社會的常態。有論者甚至認為,隨著實體機器人革命走向深入,AI正在成為新的“情感主體”“社交主體”。所謂機器情感、AI陪伴的實質是什么,對人機交互、人機關系產生何種影響?比如說,從文化視角和性別視角,應該如何看待人機情感關系呢?人與機器的情感交流,將會產生何種社會沖擊,導致何種技術風險和技術倫理問題,又應該如何應對?類似問題,已經引發諸多熱議。本次筆談聚焦“機器情感與AI陪伴的人文審度”,從哲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文學和人工智能等進行跨學科研究,拋磚引玉,以期推動該領域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第一組6篇論文由本刊2025年第3期刊發,引起學界極大的興趣和關注。本期刊發第二組共7篇論文。在《智能時代情感操控技術的三重特征解析》中,閆宏秀和羅菲圍繞“誰在操控”“操控如何實現”“操控如何呈現”三大關鍵問題,指出AI情感操控技術中的動機代理化、系統性生成與結構性隱匿的特征,主張構建適應人機復合系統的新型倫理責任框架。在《情感計算的哲學缺陷及其技術克服進路》中,孫強梳理情感識別、情感生成和人智情感交互等情感計算領域關鍵技術的哲學缺陷,提出在以人為本核心價值指導下克服缺陷的潛在進路。在《情為何物?——機器情感的哲學分析》中,史晨和劉鵬從情感與理性的關系入手分析機器情感的實質,主張打破情感幻像,走向適度情感、適度理性的人機互動。在《誰決定我們的情感生活?》中,黃柏恒以Moxie社交機器人停運引發的兒童哀悼為主要案例,揭示商業邏輯主導下情感AI的結構性情感不公正,呼吁通過認知賦權重塑技術公司與用戶的情感權力關系。在《“DeepSeek中文情感難題”與可能出路——一種“共在—預測AI”進路》中,吳雪梅指出“DeepSeek中文情感難題”表現為難以理解中文情感與難以識別語義兩方面,并提出“共在—預測AI”的解決方案,主張發展以中文共在情感為啟發的群體智能以提升DeepSeek的中文情感計算能力。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驅動的人工親密關系及其社會情感對齊》一文中,段偉文探討生成式人工智能驅動下人工情感和人工親密關系帶來的社會情感沖擊,強調超越似真情感悖論和機器貶低等數字文化批判的視野,轉而從基于“主體—他者—世界”參照三角的“社會—情感—認知”發生機制出發,尋求AI個人主義時代的社會情感對齊之道。在《風骨智能體與智能人文》中,楊慶峰提出構建風骨智能體來克服理性智能體過于強調目的和理性優先的局限,并為智能人文的研究提供一條可能的路徑。(專題特邀主持:劉永謀)
本系列文章原刊《科學·經濟·社會》2025年第5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如何應對“DeepSeek中文情感難題”是AI界面臨的一大難點,這要求我們從哲學層面思考可能的解決方案。根據DeepSeek的預測特征,DeepSeek所應用的情緒理論傾向于“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應用這一理論預測中文情感面臨兩大難題:難以理解中文情感與難以識別語義,即“DeepSeek中文情感難題”。基于對中西方哲學傳統中心物關系的研究,鑒于中文情感的本質是一種共在情感,盡管導致DeepSeek難以識別語義的根源在于預測方法,但目前AI的最優方法又只能限于預測方法。以中文情感的共在特征為啟發,發展一種“共在—預測AI”進路,通過群體智能提升DeepSeek的中文情感預測能力,或許能夠以此為突破口實現未來AI在情商、智商與審美能力的實質性增強。
DeepSeek這一國產大語言模型的出現,不僅引領國際知名大模型開源免費,極大地推進了國內各行各業的應用發展。值得重視的是,除了解決相關智力問題外,Deep-Seek所提供的情感咨詢服務也備受關注,將其視為“賽博戀人”成為年輕人的潮流。基于此,國內多款情感陪伴類AI也接入Deep-
Seek,這證明DeepSeek目前在基于語言的情感模擬這一情感計算領域表現良好。但目前也有越來越多證據表明DeepSeek在預測中文對話中的情感上存在困難。最新有研究團隊對大語言模型是否能夠預測中文對話中的“大五人格特質”開展了實證分析,對現有的DeepSeek、GPT-4與Qwen1.5等22個大語言模型與該團隊微調的Llama3-8B-BFI模型,在基于中文對話預測性格特質上的表現進行了研究①。該研究指出,包括DeepSeek在內的大模型在中文對話的情感理解方面表現較差,比如有時中文用戶對挫折持積極態度,但大模型卻會將其理解為沮喪等消極情緒,除此之外,還容易將中文對話中“我總是擔心別人對我有負面評價”理解為字面意思,而事實上用戶的真實動機并非如此,只是語言上強調感受的表達。
要解決這一困境,需應對三大問題:第一,DeepSeek預測中文對話中情感的理論與方法所導致的難題,本文稱之為“Deep-Seek中文情感難題”是什么?第二,造成這一難題的原因是什么?第三,如何能夠提升DeepSeek對中文對話中情感的預測能力?
一、DeepSeek中文情感難題
鑒于DeepSeek作為大語言模型處理情感的方式是以語言為基礎進行的,要想深入研究“DeepSeek中文情感難題”,就需要首先從方法論層面剖析DeepSeek預測中文對話的基本原理究竟是什么。根據相關研究,以ChatGPT為代表的大語言模型核心技術是貝葉斯方法論,原因在于其基本原理是“后繼標識預測算法”(next token prediction)。考慮到盡管相比于ChatGPT,作為國產大模型的DeepSeek在中文表現上更為突出,但在實現智能的基本原理層面二者的底層邏輯都為貝葉斯方法論。具體而言,貝葉斯方法
的基本公式P(A|B)=[P(B|A)P(A)]/P(B),意味著人們對未來的概率判斷,是在已知某些證據的情況下先對其給出一個預先估計的“預設概率”,再不斷以新經驗的“后驗概率”去修正“預設概率”所做出的。DeepSeek與ChatGPT一樣,在生成知識內容的基本原理上,所有語言內容都會轉化為計算機能夠識別的同質標識,通過不斷以新經驗標識修正舊知識標識以達到預測生成內容的目標。正因如此,在方法論層面,DeepSeek預測中文對話的基本原理為基于貝葉斯方法的“后繼標識預測算法”。但若要分析DeepSeek在預測中文情感時所使用的理論,則還需要在已知其使用的方法論為貝葉斯概率的基礎上,對相應的情緒理論進行分析。
當前在認知科學哲學界,影響力最大的情緒理論包括基本情緒論(basic emotion theory,BET)與情緒建構論(the theory of constructed emotion,TCE)。那么,DeepSeek在預測中文對話的情感內容時,實際所應用的情緒理論究竟是哪一種呢?要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將DeepSeek預測中文情感內容的核心特征與兩種情緒理論的核心主張聯系起來進行分析,這是因為DeepSeek實際應用的情緒理論必然需要同時滿足其預測的核心特征。經研究,DeepSeek作為大語言模型在預測中文情感方面具有以下兩點核心特征:從目標來看,DeepSeek需要以實用為目標選擇相應的情緒理論進行分析;從方法來看,DeepSeek實質上也像ChatGPT一樣是以貝葉斯概率實現中文情感對話的預測與生成。接下來,我們需要分析究竟是基本情緒論還是情緒建構論滿足以上兩點特征。基本情緒論的核心主張包括兩點:第一,根據進化心理學,人的情緒可以被劃分為基本情緒與非基本情緒,基本情緒包括幸福、悲傷、恐懼、驚奇、憤怒與惡心等①,基本情緒是跨物種、跨文化共有的;第二,情緒有自然類,換言之,每種情緒有特定的生物學基礎,可通過相應的生理信號得到識別。鑒于基本情緒論的核心主張包括以上兩點,可見,DeepSeek在預測中文情感時基于實現特征的實用目的,在進行情感識別時往往會呈現出對情緒進行標簽分類的情況。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盡管DeepSeek會基于相關生理信號的文本數據,根據基本情緒論對情感進行預測,但DeepSeek本身只能夠處理語言,而無法直接像人類等生物一樣處理生理信號。除此之外,基本情緒論預測情感的方法主要是與進化心理學相關的生物學方法,而并非DeepSeek所應用的貝葉斯方法。由此可見,基本情緒論并非DeepSeek所實際應用的情緒理論。
情緒建構論以麗莎·巴瑞特(Lisa Barrett)提出的版本最為典型,巴瑞特明確指出其情緒建構論對大腦的理解建立在預測編碼(predictive coding)理論的基礎之上,鑒于哲學上往往將預測編碼稱之為預測心智(predictive mind),因此,我們可以將巴瑞特的情緒建構論稱之為“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該理論的核心主張包括兩點:第一,根據預測心智理論,情緒是大腦自上而下的預測所主動構建的,這種構建是在過去經驗的基礎上,對輸入的當前情境的感覺實現預測誤差最小化的結果;第二,情緒是大腦為了能量的動態平衡,基于貝葉斯定理,對當下情境構建相應的情緒類別(如幸福)概念的心理事件。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鑒于“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主張情緒是由概念或者說語言所構建的,因此,這對于DeepSeek需要以實用目標選擇具有可操作性的情緒理論而言,無疑是更加契合的。更重要的是,“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中所借鑒的預測心智理論,其核心要素之一就在于貝葉斯方法,且巴瑞特在相關論述時也強調貝葉斯定理對于其情緒建構論的重要啟發。由此可見,從方法論上而言,也能夠支持DeepSeek在預測情感上以貝葉斯方法實現的方法特征。綜上,DeepSeek目前所實際應用的情緒理論從哲學層面的內在邏輯而言,更傾向于巴瑞特的“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
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進一步對Deep-Seek目前在預測中文對話的情感方面所表現的強項與困境做出哲學層面的解釋。正是由于“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在核心主張上更適用于DeepSeek的特征,因此能夠保證DeepSeek在簡單的情緒理解與情緒模擬中表現良好。之所以包括DeepSeek在內的大模型會在中文對話的情感理解方面出現預測錯位的情況,如將中文用戶對挫折的積極態度誤判為消極情緒,所面臨的最大難題事實上也源自“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應用于中文情感計算的局限性。具體而言,“DeepSeek中文情感難題”的首要表現在于“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是巴瑞特在西方認知科學哲學與情感哲學的傳統下所提出的情緒理論,而中文情感在文化傳統上與西方有顯著區別。因此,DeepSeek以“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難以處理中文情感的復雜性,特別是中文對話中的情感與價值觀。第二個表現則涉及當前DeepSeek等大語言模型所面臨的共同困境,正是由于“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也基于貝葉斯概率或者說預測方法,因此,DeepSeek仍然只是在將自然語言轉化為計算機能夠理解的標識的基礎上,基于貝葉斯定理生成內容,無法理解情感文本的語義。要想真正解決這兩大難題,需要進一步從哲學層面上分別對導致“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與預測方法之局限性的原因進行深入剖析。
二、中文情感相比英文情感的特征:一種共在情感
“DeepSeek中文情感難題”的首要表現在于,DeepSeek所應用的“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難以處理中文情感的復雜性。這要求我們從哲學層面分別對英文情感與中文情感進行研究。
(一)英文情感:以“自我”為基礎的個人情感
盡管“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強調情感具有文化多樣性,但該理論所理解的情感從哲學本質而言仍然是一種英文情感,這種情感是基于西方哲學傳統中對心物關系的理解所得出的。因此,為了深入研究英文情感與中文情感的差異,有必要首先回溯至西方哲學傳統與中國哲學傳統基于心物關系對情感的理解。西方哲學傳統對情感的現代理解可以追溯至笛卡爾,笛卡爾在《論靈魂的激情》中將激情定義為“相連于靈魂自身的知覺”,即“自我”的當下知覺。自此以來,以“自我”為基點理解情感就成為西方情感哲學的理論前提。巴瑞特的“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也延續了這種“自我”情感的理解,巴瑞特與齊奧娜·琳達(Tsiona Lida)明確指出其對情緒的理解受到笛卡爾將激情理解為知覺的影響,進而將情緒實例定義為是“自我”在特定情境下的實時心理事件。
這種基于笛卡爾的心身關系對激情的理解能夠在理論預設層面解釋“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的做法,但難以從方法論層面說明現代科學的形而上學為何支持科學方法研究“自我”情感這一關鍵問題,有證據表明只有深入心物關系才能回答這一問題。關于笛卡爾對心物關系的認識,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基于相關論證指出,盡管笛卡爾在第二沉思中明確指出“人的精神的本性以及精神比物體更容易認識”,但笛卡爾所使用的科學方法證明了這一主張是錯誤的,因為基于其機械論的有機體理論,笛卡爾實際上堅持包括身體在內的物體才是最少理智的,也是唯一可理解的。這意味著如果說笛卡爾的科學方法成立,那么在心物關系的主張上應該是物體的本質比心靈的本質更容易認識,而這一邏輯更加融貫的主張正是笛卡爾主義者尼古拉斯·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所持有的。馬勒伯朗士反對笛卡爾對心物關系的論斷,指出我們對靈魂的認識遠不如我們對廣延的認識那么完美。基于此,馬勒伯朗士明確指出為了詳細證明激情在身體與心靈中的變化,“首先有必要對物理學進行概述,接著對人體做出非常精確的描述。”由此可見,在馬勒伯朗士那里,具體需要研究作為“心”的激情時,也需要首先基于物理學與生物學對作為一種特殊的“物”的身體進行研究。質言之,以馬勒伯朗士為代表的西方哲學實質上是基于一種科學物論研究激情。而“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盡管被稱為是一種心理建構論,但巴瑞特明確表明該理論并非沿用源自哲學的民間心理學(folk psychology)研究情緒的大腦基礎,而是基于貝葉斯方法與認知神經科學對大腦的結構與功能出發,對個體情緒的生物學基礎進行研究。
綜上可見,笛卡爾基于心身關系對激情的理解證明西方情緒哲學從理論前提而言是基于“自我”的,而馬勒伯朗士對心物關系的主張,即物體的本質比心靈的本質更容易認識,證明西方情緒哲學傳統支持以科學方法研究“自我”情感。但問題的關鍵在于,中文情感是基于中國哲學傳統對心物關系的理解所發展出來的,而并非基于西方哲學傳統。因此,要想研究中文情感的本質,需要回溯至中國哲學傳統基于心物關系對情感的研究中去。
(二)中文情感:以“親親”為基礎的共在情感
在中國哲學傳統中,朱熹曾說道“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理本身沒有知覺能力,但當氣凝聚成具體形體或者說有了物質基礎后,理與氣相結合便能產生知覺。有研究表明,朱熹所說的知覺是“性命之理的知覺化的呈現”。質言之,朱熹所說的“物”并非西方哲學理解的那樣一種科學層面上作為客觀對象的物,而是指與周圍人與物之間的互相聯系中的性命體。由此可見,在中國哲學傳統中,不僅如有研究指出的那樣“心”的概念是偏心的,“物”的概念也是偏心的。也就是說,在中國哲學傳統中,與物相比,心是更基礎的,即便是研究物,也需要通過思考心的方式獲取對物的理解,因而心物關系整體是偏心的。
基于在中國哲學傳統下“心”“物”概念與心物關系都偏心,偏心意味著心物關系是以人的情感或精神為核心展開的,因而在思考中文對情感的理解時,需要以人為中心,同時貫通考慮到“心”與“物”,通過研究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由此可見,基于這樣一種主客觀融合且整體偏心的心物關系,中國哲學并非像西方哲學那樣以“自我”為單位定義情感,而是在人與人、人與物的關系中理解情感。有研究明確在存在論意義上將中國哲學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優先性稱之為一種共在存在論,這種存在論主張“共在先于存在,并且,共在規定存在”,意在強調我們“每個人都存在于與他人的共在關系中,每個人都不可能先于共在而具有存在的意義”。據此,從重視共在關系的優先性上這一點而言,我們可以說中文情感在總體上是一種共在情感,而非西方哲學傳統下的自我情感。而根據前文對中國哲學傳統下心物關系的分析,我們已知,在討論情感問題時,除了共在存在論強調的人與人的關系之外,也需要考慮到人與物的關系,因此在涉及具體是以什么為基礎的共在情感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基于心物關系進行分析。
在人與人的共在關系中,首先需要面對的是“親親”問題,之所以說“親親”也屬于心,主要因為第一個“親”是在動詞的意義上意為親近,因而屬于情感層面的“心”“。親親”也就是在性命或者說生命的意義上理解“我如何對待生我者、我生者、與我共生者”。以“親親”這一生命的共在關系為基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需要思考關于倫理關系的知識,即如何在倫理意義上推己及人以尊重他人,也就是“仁民”。換言之“,仁民”意為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心與他心之間的良好關系,也就是心際關系。因而可以說,從“親親”到“仁民”的情感思考邏輯,是從生命層面對建立良好人際關系的思考,過渡到從倫理層面對建立良好心際關系的思考。在上述人與人的共在關系的基礎上,對情感的思考還需要考慮人與物的共在關系。在人與物的關系中,儒家主張“愛物”,“愛”屬于心物關系的“心”的層面,考慮到前文已經證明“物”在儒家那里具有主客觀交融的特點,也就是說,我們是在物與自身的共在關系中理解物,本質上而言是將“物”理解為與人有關系的“事”。正因如此,國內有研究指出共在存在論研究的是“事”的世界,而非西方哲學中所定義的客觀的“物”的世界。因此,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哲學所主張的“愛物”本質上是愛與人有關系的“事”。由此可見,中文情感是以“親親—仁民—愛物”的思考邏輯,將情感理解為一種共在情感。可以說,中文情感的本質是以“親親”為基礎的共在情感。正因如此,DeepSeek以“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這樣一種英文情感的理解,處理中文情感時會面臨識別與理解錯位的困境。
三、理解語義中情感的困難:預測方法的局限性
前文已證明DeepSeek除了在理解中文情感方面存在困難之外,在理解中文情感文本的語義上也存在困難。以ChatGPT為代表的大語言模型目前尚無法理解語義這一結論,已基本成為哲學界的共識。鑒于DeepSeek在實現智能的底層邏輯上仍然與以ChatGPT為代表的大語言模型類似,要想回答DeepSeek究竟為什么難以理解中文情感文本的語義,需要對目前造成生成式AI難以理解語義的根源入手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還需要進一步研究DeepSeek無法理解中文情感文本語義的根源是什么。
首先,關于目前生成式AI為什么難以理解語義的問題。有研究指出目前以Chat-GPT為代表的大語言模型所使用的貝葉斯方法,從哲學層面上本質上基于經驗論思維而非先驗論思維。經驗論與先驗論是西方哲學史上兩種對立的理解人類思維本質的理論方案,特別是休謨問題就因果關系提出挑戰之后,進一步引發了包括康德與胡塞爾等先驗論者對先驗論的辯護。休謨在《人類理智研究》中提出:“我們關于因果關系的知識,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從先驗的推理獲得的,而是完全產生于經驗,即產生于當我們看到一切特殊的對象恒常地彼此聯結在一起的那種經驗。”休謨進一步指出“根據經驗作出的任何論證都不可能證明過去與未來相似……即使承認事物的過程從來都是這樣有規律,但是如果只憑這一點而沒有什么新的論證或推論,并不能證明將來會繼續是這樣。”由此可見,休謨對先驗論的挑戰在于因為經驗無法解釋因果概念,這意味著依據過去的經驗無法預測未來,因此先驗論所承諾的先驗原理并非普遍必然。即便是康德與胡塞爾為解決休謨問題提出的先驗論方案仍然沒有解決休謨問題。但目前生成式AI僅使用屬于經驗論的貝葉斯方法就實現了對文本內容的預測,因而不可否認至少在人工智能領域,這種經驗論的貝葉斯方法即便是基于概率對下一個標識進行預測,但也在預測文本內容上表現出了較高的智能水平。
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有證據表明,也正是因為貝葉斯方法只是對未來進行概率預測,因而導致目前大語言模型仍然無法理解文本語義。關于這一點,有研究從科學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推理方法與預測方法是科學研究中重要的兩種方法。二者的區別在于,前者得出的結論具有必然性,在科學研究中可用于構建理論模型;后者往往需要通過建立數學模型的方式進行預測,得到的結果并非必然的,而是依據后驗概率不斷修正先驗概率的預估值。鑒于此,我們可以發現這里所說的預測方法也就是貝葉斯方法,而推理方法與預測方法也分別對應于前文從哲學層面上所說的先驗論與經驗論。該研究指出當前人工智能所運用的主要是預測方法,而預測方法的局限性則在于忽視了推理對認知的重要性,這一點的表現之一就在于現有模型依據預測方法難以理解語義,特別是情感語義。也就是說,從哲學層面上而言,預測方法只能幫助AI實現人的經驗思維能力,但對于理解情感語義至關重要的先驗理性能力,預測方法是難以達到的。更重要的是,鑒于目前應用預測方法的“Transformer等模型用整數標注詞匯,忽略了詞匯在語義空間中的真實含義是多重或模糊的”,因而如果在技術層面上解決不了語義問題,那么就難以完備地構建楊立昆(Yann Lecun)所主張的世界模型。由此可見,正是預測方法或者說貝葉斯方法的局限性是造成DeepSeek在內的大語言模型難以理解語義的根本原因。
具體至DeepSeek在理解中文情感語義面臨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這一問題,則需要結合中文情感的本質特征進行研究。前文已經證明中文情感的本質不同于英文情感,其本質是以“親親”為基礎的共在情感。但DeepSeek目前所應用的“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所使用的預測方法是基于英文情感的理解做出的,以個體為單位通過預測方法實現對情感的量化研究,因而會導致在理解中文情感語義時出現誤讀現象。因此,我們可以說,DeepSeek在理解中文情感語義上存在困難的根源在于“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所使用的預測方法難以適用于對中文情感的研究。
四、一種新方案:“共在—預測AI”進路
基于“DeepSeek中文情感難題”成因主要集中在中文情感的理解與預測方法兩個方面,要想提升DeepSeek對中文情感的預測能力,就需要找到能夠解決這兩大難題的路徑。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兩大難題本身似乎陷入了一種循環。因為如果要使Deep-Seek認識到中文情感的本質在于以“親親”為基礎的共在情感,這本身似乎對DeepSeek提出了能夠理解語義的要求,然而預測方法本身的局限性決定了DeepSeek無法理解語義,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這一困境是無法解決的。之所以會陷入兩個難題的循環,是因為這種傳統思路本質上將DeepSeek理解中文情感語義的能力類比于人的先驗理性能力,而將DeepSeek所使用的“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的預測方法類比于人的經驗預測能力,以此類比,那么要想解決這一難題就只能通過研究如何協作先驗論能力與經驗論能力找到突破口。這種研究思路或許適用于英語的大語言模型場景,因為先驗論與經驗論是西方哲學傳統下對人類思維能力的理解,但忽視了DeepSeek預測中文情感需要針對性地考慮中國哲學傳統下對情感的認識。因此,我們需要從中文情感的共在特征入手思考解決這一難題的新進路。
關于中文情感的共在特征,首先需要回到中國哲學共在存在論的相關主張,以探尋DeepSeek如何能夠以此為突破口同時化解在理解中文情感與預測方法上的困境。共在存在論的基本問題是“共在”(coexistence)而非“存在”(existence),也就是說,鑒于情感的這種共在特征,每個人所產生的情感都處在與他人情感的共在關系之中。換言之,這種與他人情感的共在關系是比個人情感更基礎的存在,共在關系是確定個人情感的前提。從中國哲學對心物關系的思考,也能夠看出,中文情感并非像英文情感那樣以科學物論為基礎理解情感,因此像“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那樣僅僅以科學的預測方法研究情感是不適宜研究中文情感的。當然這并非否定基于經驗論的預測方法在實現語言預測上發揮重要作用,而是強調在“DeepSeek中文情感預測難題”方面,首先需要解決如何讓AI理解中文情感的共在特征這一難題。具體而言,考慮到中國哲學對心物關系的理解,中文情感是以“心”為基點在人與人、人與物的共在關系中以“親親—仁民—愛物”的思考邏輯展開的。因此,從理論上而言,要想讓AI理解中文情感的共在特征,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基于共在存在論,我們需要以“親親—仁民—愛物”中人與人、人與物的關系去確定個體對他人與物的情感。
那么,要想讓DeepSeek認識中文情感的共在關系,是否需要以不同于預測方法的推理方法實現呢?回答是否定的。因為盡管DeepSeek應用的“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的預測方法的局限性決定了語義識別的困難。但鑒于目前AI還屬于圖靈機的概念,因此尚且無法使其突破預測方法掌握推理方法才能夠獲取的通用數學、邏輯的先驗理性能力,因此目前AI處理大數據的最優方法還是只能限于經驗論的預測方法。況且,我們不能否認,目前DeepSeek應用的“預測心智—情緒建構論”用預測方法的確能夠幫助AI基于過去的經驗,以較高準確率實現對當前情境情感實例的預測。由此可見,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預測方法的基礎上,通過對中文情感共在特征的認識,幫助DeepSeek提升預測中文情感的能力,我們將這種研究思路稱之為一種“共在—預測AI”進路。具體而言,鑒于DeepSeek基于預測方法無法從語義上直接理解中文情感的共在特征,因此,要想使得AI理解“共在”這一點具有技術可行性,我們需要放棄讓AI理解語義這一思路,轉換成借助中文情感具有共在特征這一洞見,使得AI利用預測方法實現對中文情感共在特征的理解。具體而言,鑒于中文情感的共在特征本身強調的人與人、人與物的共在關系,以此為啟發,DeepSeek對這種共在情感的理解或許可以通過群體智能(swarm intelligence)的方式間接實現。有研究已經證明通過GPT-4o驅動的多智能體系統(multi-agent systems)以蟻群覓食與鳥群飛行為例,證實了大語言模型在驅動群體智能方面具有較大潛力。除此之外,越來越多研究表明,多個大語言模型智能體(multiple LLM agents),比單個智能體更智能。甚至有學者經由實證研究指出在涉及需要密集邏輯推理的任務時,與單個智能體相比,多智能體系統能夠提高集體的推理能力。有證據表明,群體智能除了能夠提升AI的推理能力,也能夠顯著提升基于腦電圖的情緒識別的準確率。當然,群體智能并非簡單的多模型集成或投票,而是需要將其內部機制的設計與“親親—仁民—愛物”的共在關系結構進行深度耦合,從而將哲學理念操作化。系統的目標函數需要從“個體最優”轉向“關系最優”,即單個智能體的成功不僅在于其自身預測的準確性,更在于它對提升整個集體理解能力的貢獻度,這模擬了“仁民”中個體價值在促進集體福祉中實現的思想。引入“親疏”權重以模擬“親親”關系,系統根據對話內容動態識別核心關系人物,并臨時性地增強代表這些角色的智能體之間的互動權重,從而更好地捕捉由親密關系主導的情感。建立“協商—反思”機制模擬“愛物”思想以取代簡單投票,不同智能體提出見解并交叉辯論,在多輪修正與反思后形成更具層次感的最終判斷。通過這種方式,群體智能不再是單純的技術路徑,而是“共在”理念的具體機制化呈現。由此可見,通過以DeepSeek驅動多智能體系統或許不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預測方法在推理能力上的局限性,還能夠提升情緒識別的準確率。因此,如果我們嘗試“共在—預測AI”進路,以群體智能的方式在多個AI智能體之間實現共在思維,在此基礎上,DeepSeek或許能夠以共在特征為基礎理解中文情感,以此顯著提升其對中文對話中情感的預測能力。
綜上可見,“共在—預測AI”進路對解決“DeepSeek中文情感難題”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新方向,這一方案不再困在基于西方哲學傳統的情感概念與研究思路之中,而是更有針對性地從中國哲學傳統下的心物關系出發認識到中文情感的共在特征。在批判性分析預測方法的優勢與局限性的基礎上,看到了以共在情感為啟發,依靠群體智能提升中文情感預測能力的可能性。這意味著未來以DeepSeek為代表的大語言模型在提升中文情感計算能力方面,會產生真正突破的方向或許不再是以西方哲學傳統下的個人情感為啟發的單個智能體研究思路,而是以中國哲學傳統下的共在情感為啟發的群體智能研究進路。如果“共在—預測AI”進路能夠顯著提升DeepSeek在中文對話中情感的能力,那么或許也能夠為AI在預測英文對話中情感上所面臨的瓶頸提供啟發,進而提升AI的情商、智商,甚至審美能力。
吳雪梅(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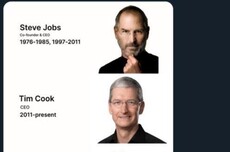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140201353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1402013531號